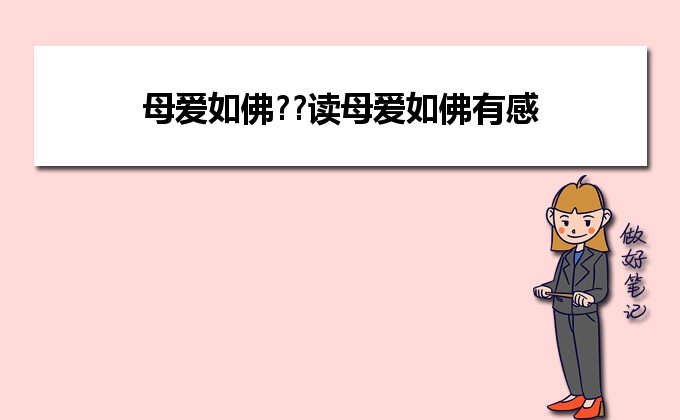《華夏美學(xué)》讀后感
在“設(shè)計(jì)美學(xué)”的課程學(xué)習(xí)中,我閱讀了《華夏美學(xué)》這一書(shū)籍,從以儒學(xué)為主的華夏文藝一審美的溫故,從上古的禮樂(lè),孔孟的人道,莊生的逍遙,屈子的深情和禪宗的形上追索,無(wú)不令我受益匪淺。
這本書(shū)令我首先了解的是——所謂華夏美學(xué),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傳統(tǒng)美學(xué)。它的悠久歷史根源在于非酒神型的禮樂(lè)傳統(tǒng)之中,它的一些基本觀(guān)點(diǎn)、范疇,它所要解決的問(wèn)題,它所包含的矛盾,早已蘊(yùn)含在這個(gè)傳統(tǒng)根源里。從而,如何處理社會(huì)與自然、情感與形式、藝術(shù)與政治、天與人等等的關(guān)系,如何理解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,成為華夏美學(xué)的重心所在。漸次論述遠(yuǎn)古的禮樂(lè)、孔孟的人道、莊生的逍遙、屈子的深情和禪宗的形上追索。
從先秦兩漢的“羊大為美”和“羊人為美”,我理解到所謂“審美”就是感知愉快和情感宣泄的人化,亦即動(dòng)物性的愉快的社會(huì)化,文化化。審美是社會(huì)化的東西向諸心理功能,特別是情感和感知的沉淀。我還了解到,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關(guān)于審美的意識(shí)不是禁欲主義,不但不排斥還包容肯定、贊賞這種感性——味、聲、色的快樂(lè),但對(duì)這種快樂(lè)的肯定不是縱欲主義的,而是要求用社會(huì)的規(guī)定、制度、禮儀去引導(dǎo)、規(guī)范、塑造和建構(gòu)。華夏藝術(shù)和美學(xué)是“樂(lè)”的傳統(tǒng),是以直接塑造、陶冶、建造人化的情感為基礎(chǔ)和目標(biāo),而不是以再現(xiàn)世界圖景喚起人們的認(rèn)識(shí)而引動(dòng)情感為基礎(chǔ)和目標(biāo),所以中國(guó)藝術(shù)和美學(xué)特別著重提煉藝術(shù)的形式,而強(qiáng)烈反對(duì)各種自然形式。
儒家美學(xué)強(qiáng)調(diào)“和”,主要在人和,與天地同構(gòu)也基本落實(shí)為人際的諧和。莊子美學(xué)也強(qiáng)調(diào)“和”。莊子哲學(xué)是既肯定自然存在,又要求精神超越的審美哲學(xué)。莊子最主要的審美對(duì)象:無(wú)限的美、“大美”、壯美。指的是不為包括社會(huì)倫理道德在內(nèi)的各種事物所束縛的個(gè)體自由和力量的偉大。而孟子的“大”指的是個(gè)人的道德精神的偉大,具有濃厚的倫理色彩。莊子極大的擴(kuò)展了沒(méi)的范圍,把丑引進(jìn)了美的領(lǐng)域。任何事物,不管相貌如何,都可以成為美學(xué)客體,即人們的審美對(duì)象。
到了六朝隋唐,美在深情。魏晉整個(gè)意識(shí)形態(tài)具有“智慧兼深情”的根本特征,深情的感傷結(jié)合智慧的哲學(xué),直接展現(xiàn)為美學(xué)風(fēng)格,即所謂“魏晉風(fēng)流”。到了宋元,則是美在境界。佛學(xué)禪宗強(qiáng)調(diào)感性即超越,瞬刻即永恒,因此更著重就在這個(gè)動(dòng)作的普遍現(xiàn)象中去領(lǐng)悟,去達(dá)到那永恒不動(dòng)的靜的本體,從而飛躍的進(jìn)入物已雙忘,宇宙與心靈融合一體的那異常奇妙、美麗、愉快、神秘的精神境界。與屈相比,禪更淡泊寧?kù)o。在文藝領(lǐng)域,禪仍繼承了莊、屈,承繼了莊的格,屈的情。禪又加上了自己的“悟”,三者糅合在一起,使格和情成了對(duì)神秘永恒本體的追求指向,在各種動(dòng)蕩運(yùn)動(dòng)中來(lái)達(dá)到那種本體的靜。而到了明清近代,美在生活。不再刻意追求符合“溫和敦厚”,而是開(kāi)始懷疑“溫和敦厚”;不必再是優(yōu)美、寧?kù)o、和諧、深沉、沖淡、平遠(yuǎn),而是不避甚至追求種種“驚”、“欲”、“駭”、“艷”等等。表明文藝欣賞和創(chuàng)作不再頑強(qiáng)依附或從屬于儒家傳統(tǒng)所強(qiáng)調(diào)的人倫教化,而在爭(zhēng)取自身的獨(dú)立性,也表明人們的審美風(fēng)尚具有了更多的日常生活的感性快樂(lè)。
讀完這本書(shū),我深刻了解了中國(guó)哲學(xué)、美學(xué)和文藝,以至倫理政治等,都是建基于一種心理主義上,這種心理主義不是某種經(jīng)驗(yàn)科學(xué)的對(duì)象,而是以情感為本體的哲學(xué)命題。這個(gè)本體,不是上帝,不是道德,不是理智,而是情理相融的人性心理。它既“超越”,又內(nèi)在;既是感性的,又超感性,是為審美的形而上學(xué)。